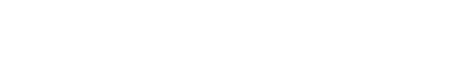河西走廊有两张名片:一张是嘉峪关。西北有句民谚:“一出嘉峪关,两眼泪涟涟。往后看鬼门关,往前看戈壁滩。”西北的人们常把嘉峪关看作“口内”与“口外”、内地与边疆的分界线。另一张是敦煌。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中心,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但敦煌又位于人们视为“口外”之地的“边疆”。作为分界线的嘉峪关与作为丝路文明中心的敦煌,二者文化边界并不一致,这恰恰体现出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是一个“过渡地带”。因此,要理解河西走廊的过渡性质,不能以单线的中原视野,而要以中原、北方草原、青藏高原、西部绿洲等多元互动的空间视角,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性视角进行观察。
一、游牧与农耕在河西走廊上的交融共生
1 、从绿洲视野认识河西走廊
“绿洲”在唐诗中已经出现,但其作为地理学概念,源出希腊语,后以“ 0asis ”通行于西方地理学文献中,中文译名曾为“沃洲”“沃野”等,现在则统一为“绿洲”。何为绿洲?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提出“绿洲学”概念的黄盛璋先生指出:绿洲是干旱地区通过灌溉而使农牧业发展的地方 , 是荒漠地带特有的地理现象 , 也是人类长期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产物。我国绿洲主要分布在西北的新疆和河西走廊两个地区 , 尤以新疆最为集中和典型。河西地区的绿洲在拉铁摩尔看来,是一种“次绿洲”,“在东、西部中间,有一片可称作‘次绿洲’的地带,特别是在甘肃西部,从兰州向西,沿南北山麓直到安西,从安西开始是艰苦的沙漠道路,西北直至哈密,再西到罗布泊。这个地理区域可以加上流入蒙古腹地的额济纳河地区和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地区”。相对而言,河西走廊上“次绿洲”的交通条件要优越于塔里木盆地中的沙漠绿洲。就河西走廊(或称河西地区)的地理范围而言,人们意见不一。按照地理学家朱兴运教授、任继周院士等学者的界定,河西地区指黄河以西,吐鲁番盆地以东,古丝绸之路的中段,东西长约千余公里,南北约百公里。大致划分为东 ( 乌鞘岭—山丹 ) 、中 ( 山丹—嘉峪关 ) 、西 ( 嘉峪关—甘新交界处 ) 三段。走廊夹处于南、北两山之间,其南部是祁连山系统,分布有林地、灌木林草地和高山草甸,涵养水源,灌溉着中部绿洲,祁连山以东西走向为主,与天山、昆仑山遥相呼应;其北部屹立着以阿拉善平原荒漠系统为背景的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北山山脉与东天山余脉相接。在南山、北山之间,洪积、冲积的绿洲星散其间,形成绿洲带。
从绿洲的角度看,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走廊。祁连山犹如一座伸进西部干旱区的“湿岛”和“绿岛”,成为河西走廊的生态屏障。祁连山脉的高山和谷地大部分海拔在 3500 米至 4000 米以上,高低不等的谷地和平原形成大小不一的草场和草甸。由于海拔高,多数地区宜牧而不宜农,游牧比农耕发展要早。祁连山曾是匈奴人的优良牧场,匈奴人称“天”为“祁连”,祁连山亦被游牧民称为“天山”。《史记》中也曾有“祁连天山”的记载。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形成黑河、石羊河、疏勒河、党河等内流河,自南向北流入沙漠戈壁,而河流的冲击扇则形成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绿洲,这些绿洲历史上常被总称为河西。
2 、廊道和基底:河西走廊的双重角色
河西走廊是以山地、绿洲、荒漠为主体的复合系统,其中绿洲系统是人类主要的聚居地,很早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历史上是众多民族聚散的舞台,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来的两千余年间,河西走廊承担了既是廊道( corridor )又是基底( matrix )的双重角色。
在走廊之上,绿洲如同一个个“岛屿”,成为商业中转站,也给过路商队提供补给。这些“岛屿”通过商路“以线串珠,以线带面”形成网状和带状分布,使得绿洲连缀起来,形成地方市场和商业网络,河西走廊亦以此为基底,成为丝绸之路主动脉的关键一段。同时,整体的河西走廊又是一个山地—绿洲—荒漠系统的地理复合体,有限的资源总量,特别是水资源约束和限定了人类的活动,难以发展出如同关中盆地的人口与市场规模,而是以一个较为广大的“面”支持了丝绸之路这一条“线”。
将视野延展到欧亚大陆,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又组成了东西交通要道上的“绿洲桥”。“绿洲桥”或是“绿洲路”,使得河西走廊举世闻名,也是其作为过渡地带的核心特征之一。
开通“绿洲桥”的重大动力之一来自于西汉王朝。 1984 年,民族学家谷苞指出,在西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一个广大的游牧区。在西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也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正是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开发出了农业区,使河西走廊将塔里木绿洲与中原农业区,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农业区联系起来,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形成。另一方面,河西绿洲农业区在实现了西汉王朝的“隔绝羌胡”作用的同时,也嵌入到游牧经济圈中,成为一个农牧接触带,促进了农牧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共生。
3 、游牧与农耕的交融地带
河西绿洲农业区一方面体现为“华夷边界”,如阳关、玉门关和嘉峪关是历史上著名的关隘,又如护卫绿洲的长城依托走廊地形而展开;另一方面,它又是游牧民以毛皮和牲畜来交换粮食的重要集市,发挥着“接驳之地”的作用,吸引游牧人群也始终参与和支撑着“绿洲桥”“绿洲路”的交通。如果没有游牧人群就近提供骆驼和马匹,连接绿洲桥的远距离交通显然是不能实现的。
正如谷苞先生所强调的,虽然对于汉、匈之间的冲突与对峙,史不绝书,但汉、匈关系的主流是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对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战争作为“特殊现象”,是史书记载的重点,但实际上,民族交往才是河西走廊上“年年月月”都发生着的“常态”。谷苞先生还指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有相当多的汉人补充了匈奴的人口;同样匈奴人口也大量进入到农区,充实了汉人人口。
河西走廊的绿洲是任继周院士提出的“山地—绿洲—荒漠系统复合体”中的一个耦合系统,自汉代之后,山地游牧、荒漠游牧始终与绿洲农业相伴生。虽然中原王朝把河西走廊的若干核心绿洲开发为农耕区,但走廊上大小不一的谷地、冲积平原、戈壁和沙漠上错落分布着众多绿洲,还有相当多的绿洲保持着农牧共生状态。在汉代设置河西四郡和玉门关、阳关之后,尽管在河西走廊上有了明显的“夷夏”边界,其中大部分作为游牧者的草原民族向西域、中亚一带移动,但是仍有大量小月氏、匈奴和卢水胡人游牧于敦煌南山,说明河西仍然与西域、中亚各民族有着紧密关联。正如巴菲尔德所说,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游牧区对于农业区出产的粮食、布匹、茶叶、丝绸等生活物资具有很强的需求,而河西走廊上绿洲农业区的形成,使游牧人群可以不必远涉中原,就近在河西走廊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等物资。另一方面,农业区同样需要游牧区的畜产品,其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也要借助游牧人群覆盖欧亚大陆的贸易圈才得以获得收益。在河西走廊上发生的这种生计与产品的共生、互补、交流形态也导致了农牧民之间文化的共生、互补与交流。
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李建宗教授同样关注到河西走廊上形成的“山地游牧—绿洲农业—荒漠游牧”错落分布的空间形态。走廊两边的山地形成了山区草原牧场,在山下的戈壁地带形成戈壁牧场,在戈壁中的绿洲上则出现了进行水利灌溉的农业区。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在进退之间对河西走廊进行周期性和交替性的控 制,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西走廊上此消彼长。当以游牧人群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势力蔓延到河 西走廊时,游牧文化兴盛一时;当中原王朝统治的“强波”向河西走廊辐射时,农耕文化在这里 开始复苏。农牧关系在时空上的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是河西走廊一个重要特点。或许在 人们的观念中,河西走廊贯穿着一条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但事实上,这条文化的分界线在历史上不时变更,很多时候甚至是模糊不清的,体现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融共生的特征。 河西走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融地带”。
二、从“过渡地带”理解历史中国
1 、“胡汉共治”中的多元化和一体化策略
以绿洲为核心的农牧交错带深刻改变了河西地区的区域化进程,河西走廊历史上出现的大小 不一的地方性政权,大多具有“胡汉共治”的特征。汉魏晋时期在河西实行的移民屯边政策,加上内地官员大族迁入等原因,使河西的汉文化得以迅速发展,河西四郡因为地缘关系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个整体。从两汉交替之际窦融“保据河西”,到西晋末年张轨“出镇河西”,汉文化在河西的传播与影响不断加强。到了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河西相对安宁,遂成为内地世家大族的重要移民避难地区,汉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并发扬光大。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是关陇集团的代表,其制度渊源上承汉魏,中继北朝的魏、齐政治,河西五凉是其间的重要中介。故陈寅恪先生称,河西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河西在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河西走廊的区域性政权也为大一统王朝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与制度资源。武威(曾称凉州、姑臧)和张掖(曾称甘州)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嘉峪关和敦煌。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武威,而不是敦煌,而石羊河流域的武威绿洲和黑河流域的张掖绿洲,也远比疏勒河流域的敦煌绿洲要大。《后汉书·孔奋列传》记:“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五凉时期的前凉、后凉、北凉均立国于凉州,隋唐时期凉州成为陇右的中心,唐代河西节度使治所亦在凉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到了明清时期,更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
从事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学者张力仁注意到在归义军时期,河西分别出现分属于不同民族的政权体系,如甘州回鹘牙帐、肃州龙家、凉州蕃汉联合政权、敦煌归义军政权等。只要有绿洲,就有人从事定居农业,绿洲为地方割据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统治基地,其社会也都由“胡”、汉人群共同构成。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占据了敦煌和酒泉两个核心绿洲;北凉政权则占据了张掖绿洲;南凉政权则占据了武威和西宁绿洲。西夏党项政权统治的核心区之一也是在河西走廊,凉州武威的“西凉府”地位仅次于西夏国都“兴庆府”。
而这些地方政权和中原、游牧政权之间发生着不同的关系,既有战争,也有长时段的和平交流,农区、草原和绿洲之间力量互动的结果使得河西走廊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色。为了适应治理区域内的农耕与游牧人群的需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往往接纳多元文化。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就是“多语并存”的多元文化区域。如现存的“凉州碑”(全称为“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一面是西夏文,一面是汉文;发行的货币,既有西夏文又有汉文。西夏惠宗时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对内大兴儒学,提倡汉文化与技术,废行蕃礼,改用汉仪。元至正八年(1348年)刻的西宁王速来蛮重修莫高窟的功德碑,就是用西夏、汉、藏、回鹘、八思巴、梵文6种文字刻成,这几种语言文化在河西走廊都有分布。
除了多元文化政策以外,河西治理者也采取一体化政策,特别是为了弥合游牧与农耕的意识形态差别,一些时期的统治者特别推崇佛教,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推手。河西最早的石窟就是在卢水胡人北凉沮渠蒙逊政权时期开始营建的,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涉及十多种文字。在吐蕃、党项、回鹘、蒙古政权占据河西走廊时期,佛教依然为各族统治者和民间所推崇,得以长盛不衰。吐蕃赞普大规模推行佛经抄译,敦煌成为抄经并向外传播的中心之一。近年,藏地一些寺院发现的吐 蕃时期的经典,其抄经人就是敦煌的写经生群体,可见敦煌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敦煌有“善国神乡”之称,吐蕃占领敦煌后,赞普赤松德赞邀请敦煌的禅学高僧摩诃衍入藏,亲自询问有关禅宗的问题,敦煌人王锡随摩诃衍一道入藏,并撰写了《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记录这一过程。摩诃衍和王锡在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布禅法,使汉地禅宗思想在吐蕃得到迅速发展,影响颇巨。在汉僧与印度僧人的大辩论中,摩诃衍与王锡一道阐述了汉地禅宗的见解。河西走廊通过佛教成为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原的文化纽带,佛教也是不同民族的统治者高度重视的政治资源。
2、河西走廊对于民族格局、历史疆域形成的作用
无论是农耕政权还是游牧政权入主河西走廊,都要依凭类似的生态——文化因子;山地游牧、荒漠游牧和绿洲农业都能在这里获得相互理解的渠道,形成“胡汉共生”的多元文化格局。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曾提出,“吐蕃北上”和“蒙古南下”是奠定中国西北民族格局的重要力量。周伟洲教授继承并发扬了这一观点,认为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受到四大文化区的相互影响:中原文化区(以农业为主),甘青文化区(农牧交错)、蒙古高原与天山以北的文化区(以游牧为主)、天山以南的文化区(绿洲定居农业兼营射猎)。其中甘青文化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 是与其他文化区的分界带、接触带、缓冲带以及融合带。
这一过程中,最为显著地影响中国历史“大一统”进程的就是“凉州会盟”。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爷阔端在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为什么选择在凉州进行会盟?除了凉州是蒙古游牧势力南下青藏的战略要地,更为重要的就是蒙古世俗贵族和西藏僧侣高层在这里找到了彼此所需的政治与文化资源,使得相互理解及合作成为可能。据藏学家马进武先生考证,在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之前 , 阔端身边已有几位藏传佛教僧人 , 但在举行祈愿法会时 , 均由也里可温(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和萨满教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迦班智达到来后,其关于佛教的讲授令阔端叹服而更加崇佛。于是下令祈愿法会改由萨迦班智达为首的佛教僧众坐于上首,率先祈愿。另据史金波教授的研究,阔端在见萨迦班智达之前,已在西夏故地凉州接纳和弘扬藏传佛教,为凉州会盟奠定了思想和信仰基础。在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在《告蕃人书》中明确指出,蒙古汗国势不可挡,顺服其统治乃是大势所趋。在凉州,蒙古贵族的精神世界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西藏高僧看到了蒙古武力的强大,之后,萨迦派在雪域高原的教派竞争中也因此获得了优势。
3、作为“过渡地带”的河西走廊与“绿洲路网”
河西地区东接中原、北望大漠、南达青藏、西通天山,恰好是处在内陆欧亚“十字路口”的交通枢纽,处于独特的区位。河西“绿洲路”除了“丝绸之路”的主路外,另外两条道路是“河南路”和“居延古道”。“河南路”亦被称为“吐谷浑道”“羌中道”“青海道”,它以西宁和张掖为枢纽,从河湟谷地的西宁往西,循青海湖北部,沿柴达木盆地北缘,穿越阿尔金山的嘎斯口到达新疆若羌,承东启西,通达南北。而“居延古道”则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自张掖沿弱水(今黑河)—巴丹吉林沙漠—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蒙古高原,或者从居延海往西抵达东天山。而最便捷的道路则是东西方向的“丝绸之路”。这一“绿洲路网”也属于整个欧亚大陆交通路网的一部分。
绿洲路既有军政交通的功能,也是商贸交通之路和文明交往之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队,若从关中平原、北方蒙古高原、中亚两河(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绿洲三个方向出发,敦煌和吐鲁番则大致处于三方的平均距离区间,三方商队在此形成交汇。因此,河西走廊与东天山的连接区就成为欧亚十字路口的“枢纽”,来自草原、农耕区和绿洲的商人在这里休整、居留,促成了民族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古时期的“西域”是世界多元宗教、文化的交汇处,仅以宗教而言,中国的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就此提出了“陆上地中海”的概念。敦煌和吐鲁番是“陆上地中海”的核心港口,某种意义上,“敦煌—吐鲁番学”成为反映“陆上地中海文明”的考古学。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走廊成为“华戎交汇”之地,不少从事远途贸易的中亚商人在此定居繁衍,从敦煌至凉州的绿洲城市里,“胡人”聚落绵延不绝。如唐代敦煌附近的从化乡是粟特人村庄,人口达 1400 余口,兴胡泊是昭武九姓的“胡人”聚居之地。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正是大量西域人口聚居河西的反映。唐以后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敦煌时期,“华戎交汇”的场景被大量描绘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上。正如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没有第二个。
三、从河西区域经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对于各民族的民间交往,季羡林先生于《在敦煌》一文中有极为生动的表达:
“我曾想到,当年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这一带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有的赶着羊群、牛群、马群,逐水草而居,辗转于千里大漠之中;有的在沙漠中一小块有水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努力劳作。在这里,水就是生命,水就是幸福,水就是希望,水就是一切,有水斯有土,有土斯有禾,有禾斯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生存。在许多洞子里的壁画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从人们的面貌和衣着上就可以看到这些人是属于种种不同的民族的。但是他们却站在一起,共同从事什么工作。我认为,连开凿这些洞的窟主,以及画壁画的艺术家都决不会出于一个民族。这些人今天当然都已经不在了。人们的生存是暂时的,民族之间的友爱是长久的。这一个简明朴素的真理,一部中国历史就可以提供证明。”
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游牧与农耕在此交汇,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恰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在河西走廊的历史上,既有中原农耕政权占据河西的时期,也有游牧政权占据河西的时期,或是出现游牧和农耕政权各据一方的情况,还有河西绿洲自我发展形成“胡汉共治”格局的时期。同时,在历史的演化进程中,只有在“大一统”时期,河西走廊作为“十字路口”,作为游牧区、农耕区之间的枢纽,才最为繁荣。
在河西的历史上,各民族在往来互动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和交往格局。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现象从大量描述河西风情的唐诗中可见一斑。例如王建的《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
汉家无人开旧道。
边头州县尽胡兵,
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人家皆已没,
年年旌节发西京。
多来中国收妇女,
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
相学如今种禾黍。
驱羊亦著锦为衣,
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
那堪绕帐作旌旗。
城头山鸡鸣角角,
洛阳家家学胡乐。
虽然诗人以中原人的视角表达着对凉州陷落的慨叹,但诗中生动展现着“胡”、汉人群的通婚、社会交融、农牧生活方式的转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从国家视角看,酒泉的钟鼓楼有四向券门,分别题写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城楼二楼的东西两边各自高悬“声震华夷”“气壮雄关”的匾额,与十几公里外、嘉峪关城楼上“天下第一雄关”的楼匾遥遥相对,这是河西走廊作为国家通道的历史明证。具有“过渡地带”特征的河西走廊是“南北统一体”的“汇合”之处,其中一定蕴含着重新发现和解释中国整体史的可能性。由此,我们需要调整以往的研究视野,重新认知民族交往的地域属 性,理解民族交往也是在一个地域形成过程中的共同体经验。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该被理解为诸多世居民族各自历史的集合,而是多民族共享一个地域、在民族交往互动中求得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河西区域经验出发,我们可以尝试以一种“区域关系史”的新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黄达远,从事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沙武田,从事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与考古研究。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阐释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之《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